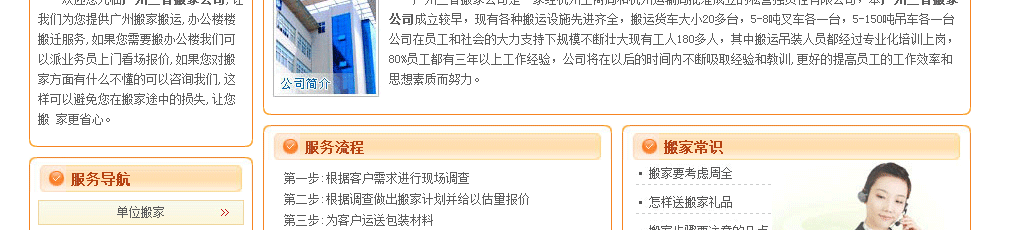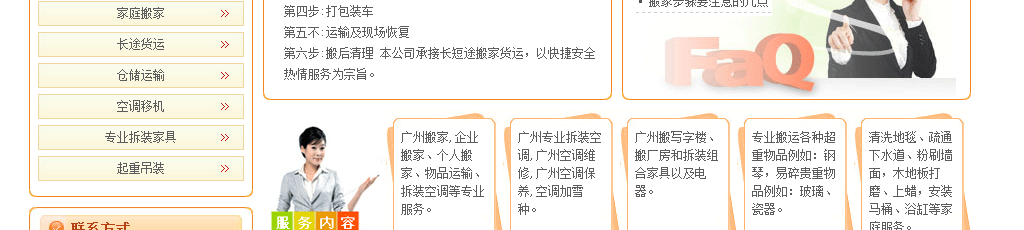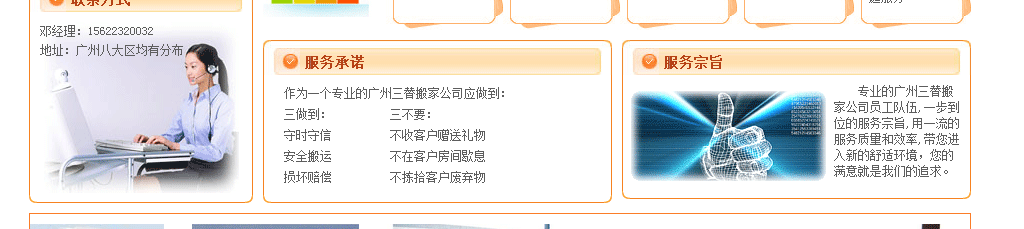,在胡同里横着走。
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只电饭锅,用一根塑料绳拴住锅环的两端,吊在胸前。左侧的胳肢窝下,夹着一只压扁了的硬纸盒,纸盒原是装电视机的,大得像扇窗户,只能半拽半拖着一步步挪;右侧的胳肢窝下,夹着一捆废报纸,绳子没系紧,走几步就得拢一拢;左手抓着一只电热水瓶,右手是一只塑料板凳;后背也没闲着,驮着一只露了个洞的编织袋,犹如背了一座小山在身上,鼓鼓囊囊的直打晃。如果不是由于两只脚得用来走路,脚背上那点空地,也能派上用处。
李大恨不能生出一百只四肢,把一切能拿的东西十足都弄走。明天早晨不弄走,明天就啥也剩不下了。他身上的东西真实 未审是太多了,粘糊糊地揭在身上,像是长出一层肥膘,一走一喘。李大曾在马路边餐馆的玻璃水箱里,见过螃蟹横着走步。还见过垃圾袋里的螃蟹壳,一堆大脚小脚毛脚钳脚,只长脚不长肉。他把身子横了过来,一步步挪蹭,
果然,大包小包都像蟹脚长回了蟹壳上,乖乖跟着他走了。他看不见死后,听着摆布有响动,就得紧贴着墙根儿,把人影让过去。李大喜悲黑天,路灯亮起来的时分,这个乡村就换了一副面貌,变得和气了许多。灯光照着墙角的垃圾桶,像是藏着金子,在私下一亮一亮。
抵家已经是深夜了,李大怕自己的样子容貌吓着酣睡的妮子,站在门外,把身上的货色一样一样卸下,再蹑手蹑脚地把东西拖回屋里去。如果留在院里,明天连根毛儿都见不着了。
这个城里不像城里、农村不像农村的犄角旮旯,谁弄到自家碗里就是个菜啊。
编织袋哗啦一声漏了底,弄出好大响声。屋里灯亮了,栓子揉着眼,含混看着散了一地的东西,说:嗬,爹发家了你啊。
李大舀起一缸凉水灌下去,插空说:正遇上有搬场的,这城里人,啥都扔。
栓子召唤他吃饭,一边扒拉着地上的东西,踢一脚,说:咋没弄个电视机回来?
李大喊哧呼哧喝粥,好轻易腾出嘴来:我借念捡个脚机呢,好往家挨德律风。
妮子醉了,跳下地,冲着一个绒毛狗熊奔去。狗熊的毛都掉了,像条癞皮狗。妮子牢牢抱在怀里,说爷爷你真行,你是个死蛋白叟,天天给我好东西。
妮子来城里上学不到一年,此外没学会,学会说生蛋老人。你胡扯个啥,李大斥责妮子。我要会生蛋,还要你爹妈干啥?睡去睡去!妮子不睡,蹲地上,二心翻拣着那堆纯物,想再找点啥。李大放下碗筷,心想今儿的辛苦真是值当得很:
一双半新的皮鞋,只是鞋尖开了线;一双旅游鞋,除鞋帮上有个烟洞,硬朗着呢;一件带拉链的羽绒服,只是拉链坏了;一条毛巾被,被角上一摊污迹,洗干净了和新的一样;电饭锅怕是进了水,再不就是电源打仗不好;电热壶就算真坏了,也能当个凉水壶用;那塑料板凳一个腿儿也不缺,李大坐上去使劲晃都没塌……这一件件一样样,哪一个都是好东西啊,过日子的好东西,缺了哪样都过不成日子的东西,怎么说扔就扔了呢。
李大对这一天的收获很满足。撂下碗,倒下身子打盹儿就上来了。
含混入耳得栓子在问:爹,将近秋收了,你啥时刻回老家嘛?七亩地的玉米,连砍带掰,少说得收上十来天,你知道凤梅在人家伺候老人,走不了,我天天在外送水请不下假,你要走,我得早几天买票……
李大不搭嘴,跟着就上来了呼噜声。
实在李大很少去城里的胡同。那些老房子里的人家,日子过得精致,好容易攒下了报纸瓶子,自己就上成品收买站卖钱了,哪怕是一根钉子,也别期望老头老太会扔出门去。
李大自有李大的地皮儿,那是一片流油流蜜的上好地块。每天一大朝晨一夜去遛一趟,他从没有空着手回来过。
早半年前,李大头一回扒拉墙角边的塑料垃圾袋时,手指头抖得凶猛,脑门上憋一头汗,才算把袋子解开了。袋子里头都是些菜叶烟头啥的,一股馊味呛得李大偏偏过脸去。李大挑出一只压瘪的易拉罐,起身要走,眼前溘然亮了亮,不由得朝塑料袋探下头去。
菜叶下暴露一只小盒儿的角角,没开上盖,亮出一截表链,银闪闪的。李大的心怦怦跳,四下张视,手哆嗦着,小心把盒子掂了出来。打开盖子,见着杏儿那大的一块手表,嵌着一圈金边边,躺在李大的掌心里。李大把表贴在耳朵上,一点动静没有,难道是个坏表?可手名义上好几根长针短针,刷刷走得欢实,看不出几点几分。李大愣在那里,挪不开步了——放回去?傻呢,其实不舍;拿走吧,此日上掉馅饼的功德儿,该不是有人下了个套?李大觉得自己像是捧了一块按时炸弹,一动不敢动。
这表是拣的,谁拣回谁。李大对自己说。就像在地边上拣了个萝卜、草窝里拣了个蘑菇,给谁送归去?不归自各儿归谁?那才叫撞大运呢!老话说道不拾遗,说的是人家遗落的东西不要拾,可要是人家抛弃的东西呢,你不拾也有别人拾啊,拾起来就成了好东西,不拾起来,让它留在垃圾袋里头,回首就进了垃圾场。李大把胸脯挺了挺,心里有了底气,喜孜孜抬头打量那块表,逆手用袖子把表受子上的汗迹擦了擦。
垃圾袋跟前那栋粉黄的房子,窗户忽地打开了,一个烫发的女人探头对他喊道:喂,拣垃圾的,你弄完了可把袋子系上口啊,别弄一地净!
李大许可一声,敏捷地把腕表揣进了衣兜里,拔腿就跑。
这表是拣的,不是跟人要的。李大一边跑着一边对自己说。伸脱手跟人要东西,就成了要饭的。李大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,不是要饭的。灾歉岁才要饭,有人就是饥死也不要饭。李猛进城来给儿子带孙女,趁便找点活儿干,不是来要饭的。老家的麦子都快熟了,城里的人吃不上那样的新颖麦子,用得着进城要饭么?李大没有伸手跟城里人讨手表,是这块手表非要跟着李大走,李大想躲都躲不开呵。
今后,李大有了一块亮晃晃的大手表,空旷地套在细瘦的胳膊上,时不断得往上撸一撸。李大爱好高高地举起胳膊,在空中划上一个大圆圈,然后在眼帘子底下愣住了,再低头看表。那会儿他盼望方圆的人都能看到他的表,所以把胳膊都举得酸沉了,还是看不敷。李大匆匆发现,平常忙集的日子,叫一块表给管住了,人都跟着手表上的点儿走,它
说到面了便该用饭,它道到点了就该睡觉,那腕表可比村少利害多了。
过了好几天,妮子从黉舍哭着回来,说每天上课都早退,让教员批驳了。
李大才发明,本来这表走得禁绝,整慢了半个时刻。妮子哭着,李大笑了:公然这表是人家扔了不要的,不是李大偷来的!
就是从那以后,李大狠狠惦念上了路边的塑料垃圾袋。谁人名叫“秀水花园”的小区里,一栋栋二层三层的小洋楼,一早一晚,家家城市按钟点,送出来一包包玄色的垃圾袋放在门前。不看不知道啊,有好几次,李大解开袋子,把自己吓一大跳呢。
李大可是有活儿干了。李大拣着手表不说,顺带着还拣了个工作。这个“工作”可比李大先前的“工作”强多了。每天在小区里转悠转悠,就把“工作”干了。不明白的人呢,管这叫拣垃圾,明白的人,就知道李大是在拣钱呢。
李大进城的头两个月,“工做”换了好几个。栓子给他部署的活儿,是接送妮子上下学。栓子和栓子媳妇进城打工几年,放在老家的妮子就到了上学的年纪。凤梅非要把妮子接到城里来,说这有个打工者后辈小黉舍,膏火不加钱。栓子和风梅租了房,让李大来给妮子做饭洗衣,城里坏人多,妮子高低学,没小我私家接送,说拐卖就被拐卖了。栓子的
娘早几年抱病死了,就靠李大守着家和地。李大底本不想进城,栓子的两个弟弟锁子和链子,嫁了媳妇都生的男娃,李大不在老家抱孙子,来这带孙女,让人笑话。栓子一个劲地催,李大心里一百个不畅快。栓子电话里说,来嘛来嘛,麦子都种下了,还无能个啥?城里有的是活儿干,你来了准保就不肯走。李大这才动了心理。
李大坐了汽车又坐水车,下了火车又坐汽车。进了乡,才知道城里的汽车不叫汽车,叫公交车。李大认为这个名儿刺耳得很,让他想起春季的母猪跟母牛们干的那些事儿。公交车哼哼唧唧喘着气,缓慢悠悠走一站停一停,处事儿的时光可比母猪长很多。从车窗往外看,一堆一堆的下楼都往天上堆来,高得只怕是要塌下来,看得人颈子都快断了。
街上挤谦了小汽车,蝗虫似的一堆一堆趴着,一会又哗地蹿出去,一辆接一辆,一个城的马路都飞着盖着蝗虫同党,看得人眼都花了。来接他的栓子一路上絮絮不休地谈话,告知他这儿那儿的花样和来源,这儿那儿都是些惹不起的衙门。李大晕晕地想,这城里果真是个好处所,这儿那儿,街角角里、墙缝缝里,哪儿哪儿都躲着干不完的活计…
后来栓子说到了到了,李大一脚迈下车,人就傻在那边。
车站劈面,破着一个铁皮做的牌牌,写着“六里庄”。牌牌下,一条高下不服的水泥路,路边的电线杆子、矮矮的红瓦房黄泥墙、院墙里的猪圈鸡窝、门前趴着的瘦狗垃圾,怎么瞧都跟老家没两样,让李大认为回到了李家庄。
这叫郊区。不住郊区,能住哪儿呢?栓子说,城里的房子一个月上千块,我微风梅俩人一月挣的交了租金就没饭钱了。这地儿可比城里强,你往东边儿看,风梅就在那上班——
顺着栓子手指的标的目的,李大又愚了。
村子的东边,隔着一条小河,是一条长长的白栅栏,栅栏上攀着一道道绿叶,一丛丛粉红的花骨朵,开得得意洋洋;透过栅栏的缝缝,看得见一大片一大片矮壮的菜地(麦地?),一座座两层楼三层楼的小房子,就盖在绿地中心,一座房顶紫蓝,一座房顶鲜红,一座房顶碧绿,屋顶上没有瓦块缝缝,色彩一整片一整片,家家门前都有雕花的黑铁门,水池里喷着雾一样的水柱,跟片子里的本国房子迥然不同。
凤梅就在那家干活儿,蓝屋顶的那家。栓子的声音有几分喜气,忽又低下去。人为很多,就是不让回家。爹你来了就好,我就塌心了……
李大没好气儿打断他说:你塌心我不塌心!撂着家里的麦子,上城里闲呆?有这工妇,几头猪都出栏了。还有你两弟三弟的娃呢,都说我偏疼眼儿……
栓子赚着笑,把行李卷往脖子上耸了耸:那是眼气你进城呢,怕你受罪来了。
李大冷静脸,跟栓子走了半里地,停在一扇歪倒的木头门前,院墙塌了半截,有妮子尖尖的笑声奔过来。李大忍不住再回头,往河哪里的白栅栏处看,一大片飘在树尖的小楼屋顶,五彩祥云一般,咋看咋就不像是人住的房子,是供仙人的地儿……
那叫个啥呢?李大抬抬下巴,指着河何处的房子,冷着脸问。
那是——“秀火花圃”,栓子一字一句问道,那都是有钱人住的,叫个甚么别薯……
李大用鼻子哼了一声:白薯白薯,没据说还有叫别薯的呢!
那时辰他但是没眼光呵。李大厥后才知道,这些个别薯扔的皮儿,就能把他的屋子填满,吃不了还兜着走。
李大进城后半个月,自各儿偷着找下了第二个活计。那些天,他趁着妮子上学的工夫,远近十几里地都散步了遍。侦察的成果,让他的绷直的腰塌下去半截。饭店餐厅招小工刷碗端盘子、发廊招洗头妹;再就是电工水工瓦工,都是技巧活,还要啥上岗证;建造工地招挖沟运土的力工,老板看他一眼就乐了,说老爷子你来干啥?这儿不是敬老院。他在农贸市场的菜摊前站一站,摊主发话:买点儿啥?不买别挡道。听说摊主都是原来村儿里的人,搬进了当局盖的楼房,早不种地了,像他一样,成天揣摩着找活儿干。一个外来户下车伊始,在老户眼里,跟打家劫舍的强盗没啥两样。你要能有活计,让人吃啥?天底下有人饿着才有人吃饱,这点情理李大年青时就明确。
活计活计,别看这城里楼多车多,可门也多,能挣钱的活计,都让人关在门里头了。李大蔫蔫地晃荡着,也不知怎么的,就绕太小河,走到“别薯”的大门口去了。
“秀水花园”的大门派头得很,牌坊一般高,圆拱门上写着烫金的字。黑漆雕花的铸铁大门前,横着一根白色的木杆,小汽车到了门口就被拦下了盘问。大门边站着个衣服上沾满油漆的中年汉子,像是在等人。李大端详他,他也把李大上下打量一番,走过来问:先生傅,会筛沙子不?李大吓了一跳,一时忘了答复。那人又问一遍,李大忙说会会
会,筛沙子有谁不会呢,你让我筛金子也会。那人说一天二十块,干不干?李说干干干,大门口的保安说了几句话,就让李大跟着他走。
李大头一回迈进这个叫“秀水花园”的别薯,路边上一丛丛吊钟似的黄花,晃得人眼都睁不开了。树丛里一栋栋的斗室子,粉黄色的墙,不锈钢的窗雕栏阳台雕栏,一里墙普通大的玻璃窗,在太阳下就像一只只金匣子;李大的脑袋不敢治动,觉得这秀水花园全部儿都是黑糊糊的。路面不知是用的啥样石头,亮得能映出人影儿,清洁得连只蚂蚁都没有,吐口痰上去,怕都打滑呢。李大的脚步有些晃荡,走得脚后跟板筋,像是脱鞋上了饭桌.一不警惕会把碗踩碎了。别薯啊别薯,这别薯真是个好东西,原来活计都在这别薯里藏着呢。
粗沙堆在一栋空屋子门前的院子里,东一摊西一撮的。房子正拆修,砸墙凿洞工程不小。工头对李大做了交代,李大就静心干活。别看李大过了六十,一袋麦子上肩,甩条毛巾一样不费劲。一会儿工夫,李大就筛出了一小堆细沙子。再把粗沙归拢了,铲到院门外,打扫得整整洁齐。吸烟歇气儿时,李大坐在院子的台阶上,眯眼瞧着自己筛的那堆半人多高的沙子,小山一样冒着尖尖。太阳哗啦啦铺下来,平川起了一座金山,细金饰软,金黄金黄,像是刚磨成的新鲜玉米面;再远些看,像场院里翻晒的麦子,一粒粒熟得实沉。一时间,李大真的弄不清那是沙子还是麦子了。他忍不住短身抓了一把沙子,在鼻子下闻了闻,马上松了手。沙子从他的手指缝里泻出去,变得水一样没有颜色。沙子怎
么能和麦子比呢?他笑话自己。玉米面和麦子都是有喷鼻味的,那种喷鼻味,是青草麦秸鸡粪柴禾还有太阳晒热的地盘、全部村子里的人味儿,搅在一路的味道。是那些饿死过去的人,闻一下就会活回来的滋味。可沙子呢,啥味儿也没有,再细的沙子,捏着也磨手……
筛了两天沙子,筛得李大胆战心惊。一到午时和薄暮,李大就得像做贼一样溜出去接妮子放学,给她做完饭,自己顾不上吃就得一路小跑回来。到了第三天,一早还没动工,领班黑着脸走过来,甩给他一张五十块的钞票,说沙子够用了,你不必再来了。李大接过钱,赔着笑对工头说,有啥整活儿,还找我吧。工头甩脸走开了。李大转身看着自己筛
下的沙堆,土黄土黄的,像个没人烧纸钱的坟包包。
李大悻悻站起来,慢吞吞地走。这别薯既然是出去了,就不闲着出去。进来了,再进来就易。李大背动手,成心走得慢,感到有点像村长了。不让干活了,看看还不中么?
这一看,李大就看闻名堂来了,给自己找了一份没人能辞得了他的活儿。 李大牵起妮子软软的小手,勤懒趿拉着鞋跟,往村外的小学校走。离校门还有几丈远,妮子就挣开他,小鸟样欢欣鼓舞飞进去了。李大弯腰捡起一片纸,捏在手里抖了抖,哗啦哗啦响。别小视一张纸片,成麻袋的食粮,也是一粒粒攒下的。如今李大的眼睛尖得像只老风筝,一根皮筋儿都.想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过去。不外,这条路走的人多,拣东西的人也多,就像收了秋的庄稼地,剩不下几根玉米棒棒。李大的“上班”所在在秀水花园,天没亮或是天黑了才有活儿。只是几个保安像狗似的在小区来回闲逛,专逮李大这样黑天出来淘宝的人。一见是李大,保安举起电棍就撵。李大说:猫丢了,找猫呢!保安说,是找死吧?你看看我像啥,像猫不像!我就专门逮你这样的耗子!所以李大见了
穿礼服的保安就发怵。
不外,猫和耗子的那点花招,李大看得多了。没过几天,李大就在白栅栏那儿寻到了一个断了一根铁条的小口,刚能钻得过一个肥人。李大把铁条原样实着安上,拣下了东西,把铁条一卸下,就从阿谁口儿塞曩昔了。栅栏下有条小道,临着河岸,沿着河绕一个大弯儿,就到了出租屋的村口,运点儿东西,神不知鬼不觉,不是隧道战也是沙家浜的
程度啊。小猫就是眼再尖,也逮不着李大这样的老耗子了。有一次李大拣着一只老式半导体,回家鼓捣鼓捣,来回换了好几个拣来的电池,半导体忽然畦地响了,差点没震到地上。当前李大白日没事儿就听半导体,一次听着个词儿叫贸易机稀,李大心想,为啥有人能拣着东西,有人拣不着,这里头也有个商业秘密呢。
不出半个月,李大就把秀水花园的垃圾摸出了门道。干一行爱一行,垃圾也像庄稼地,得人居心侍候。好比有的人家喜欢在夜里往外扔东西,要是第二天一早门前干净了,第三天就接着扔。这儿的废品收购站离得远,外头收废品的板车也进不来,有的人家,用完的塑料油桶饮料瓶子、纸箱报纸,都堆在门口,等着一早保洁员来拉走。李大得趁着
这个空儿,赶在保净员之前动手。下手早了,本来好好的东西,眼睁睁看着酿成了垃圾。有一回,逢着一家门前扔了一只沙发,李大往上一坐,身子塌下去半边儿,找不着人了。再玩弄,原来是合着的,一翻开就是张床。李大回家熬到三更,拿了两根绳去了沙发那儿,一口气把沙发举起来扛在了肩上,挪到了栅栏边,用绳索把沙发绑上,吊起来,人钻到栅栏外,当心着一点点拉拽,费了牛劲把这个沙发弄出了栅栏,而后再背着驮着,愣是把沙发运回了六里庄。
如今,李大经常坐在沙发里,打开半导体,喝着温水瓶里的凉水,眯眼养神。李大觉得城里真是好,家里缺啥,只要腿脚勤劳,拣就是了。马路上拣钱不容易,拣东西可有的是;只要不嫌旧不嫌破不嫌没脸面,拣着拣着就能置上一个家,家什齐备得可比村长家海了去。
那只旧半导体,得用一只手死死按在耳朵上,才能听见响声;一时没了动静,使劲地拍一拍甩一甩,就会像村口的喇叭似的,哇地喊得人一哆嗦。
怨不得大家都想进城呢。
这会儿,李大夹着一起拣下的纸片和空塑料瓶进了村口。李大走得大摇大摆,手里的东西甩得招摇,像是刚从超市购物回来。李大每次进村都居心如许走,他不觉得拣垃圾有啥丢人。脸在自家脸上。自己不觉得拾人,还能把他人的脸丢了?
树下谁人瘸子招呼他:又拣破烂儿呐!李大心里有些不干脆,回嘴说:跟你说几回了,这不是褴褛儿,都有效!
瘸子嘲笑着:嗬嗬能得你,你当你是环保局局长呢!
李大推开自家院门进屋,记了直腰,一仰头就撞在一只啷硬的塑料袋上,碰得脑门儿痛。如许的塑料袋有十几只,挂在一根专门拆架的竹竿上。李大闭着眼,都能摸出里头的东西。这一只袋里是林林总总的玩具,光是失落个轮子、不会动的小汽车就有十几辆,缺胳膊、正了脑壳的娃娃就有七八个,还有能写字的塑料板、长耳朵绒毛兔子、拼图的塑料块块、秃顶的彩色铅笔、戴着头盔的飞翔员(瘸子说那叫袄特慢)……
李大拣回来.用河水洗干净了,在太阳下晒干,跟新购的截然不同。如果都摊开在地上,一屋子都摊不下,像开了个玩具展子。带回老家,每样都是稀奇物,看那两个龟孙子还不抢得打斗。那一只袋里是各类绳儿,长的短的、卷的曲的、圆的扁的,松紧带猴皮筋塑料绳,都是过日子少不了的;有一卷花花绿绿的彩带,他亲眼看着窗子里那家人,从大捆陈花上解下来,转手就扔进了垃圾桶。彩带像是绸子的,鲜明滑溜,他盘算带回老家,过年时走亲戚收礼,缠上几道,那礼物看着就不知有多珍贵了。还有衣服,秋夏秋冬都齐了,光是帽子就几十个,毛线帽皮帽草帽布帽棉帽,能把半个村庄的脑袋都罩上哩。棉袄是大件,一件撑死一个塑料袋,挂得满屋子叮当。
小屋子的那点空场,已快填满了,有点转不开身了。除了吃饭睡觉的地方,处处都塞满了东西。不像个住家,倒像老家那个化肥厂的堆栈。李大也忧愁,不知怎么把这些东西搬回老家去。纸盒报纸塑料瓶酒瓶废铜烂铁,能卖的早已都卖给废品站换钱了,剩下的都是不能卖的
东西。李大发现,其真不能卖钱的东西最有用。比方鞋,棉鞋凉鞋胶鞋皮鞋拖鞋游览鞋男鞋女鞋童鞋……隔三岔五地,李大就可以从别薯的垃圾袋里,拣出一两单半成新的鞋,刷净了、缝一缝,把脚伸出来就可以穿。拣了半年多,巨细尺码都齐全了,锁子穿不了有链子,链子穿不了有链子,锁子媳妇,就连两个孙子长大了上教穿的鞋,都提早准备下了。现在栓子这租屋的床底下,塞着三只满满的编织袋,内里满是形形色色的鞋。一次李大在城里打工的一个侄子来看他,给妮子买了生果,妮子吃得高兴,当下就说:我爷爷床底下有很多多少鞋,我让他给你挑一双高跟儿的!李大疼爱得神色都变了。鞋不能卖钱可比卖钱更切实,乡村人身上最爱坏的就是鞋,谁能舍得穿新鞋下地干活?可李大不花一分钱,就把一家人春夏秋冬的鞋全包下了,每双鞋的式样都比老家的鞋强一百倍。这后半辈子,全家人的脚都有了下落,李大枕着一床底的鞋睡觉.日日睡得平稳。
就是苦了七岁的妮子,李大叹口气。自己有了这份工作,就像上了磨的驴,终日围着秀水花园转圈儿,恐怕落下了好东西,没工夫给妮子好好做过一顿有汤有菜的热饭。
忽然听瘸子在窗外喊道:李大啥时辰回去秋收啊?拣破烂儿拣得孙子都不要啦?
李大不爱理睬瘸子。瘸子整天也不干活,还老下馆子抽好烟,看着不像端庄人。这几天瘸子动不动就往李各人的门口凑,让李大烦得很。
瘸子把门推开一条缝,探头说:小区东北角上,有一家正换防盗窗,卸下的锈铁条在门口堆了半人高……
李大看着棚顶,眸子子转了转,哼了一声。
瘸子又说:搞卫生的,嫌铁条太沉,小车拉不动,给我透了个疑儿。
李大从床上坐起来:你咋弄得动哩你?物业干啥吃?
瘸子嘿嘿一乐,说:物业固然管运,以是到了明儿早上,你想弄也弄不成了。
李大心里琢磨,自己要是去了,少说得花上两个钟点,妮子一人在家咋办?想了一会,对瘸子说:你想弄你弄去吧,栓子今晚加班回来晚,我得在家守着妮子。
瘸子没说啥,甩给他一收烟就走了。
李年夜正在床上收一会呆,突然了打定主意:怎样也得寒舍多少天功夫,
回老家去春收,趁便把这一屋子的东西弄归去,把屋子腾出空儿来,再接着拣就好办了。
天黑下来,妮子下学回来,吃了晚饭就趴在桌上的台灯下写功课。
这只台灯也是拣的,瓷瓶托个粉纱灯罩,难看,就是灯胆忽闪忽闪的,一会儿明一会儿暗,弄得李大的心里心神不宁。李大不由得往窗外看,那堆小山似的锈铁条,在远处的背后一明一亮。
李大抬手看表,算上慢下的半小时,也快九点了。瘸子比李大有招,意识好几个保安。再晚一会儿,铁条就该让瘸子弄走了。
李大坐不住了。招呼妮子洗洗睡下,在里面把门反锁了,就往河滨走。出门时觉得墙根下有个影子一闪,揉揉眼,一根电线杆像小我杵在那里。
到了栅栏下,李大把铁杆子卸下,敏捷地钻了从前。按着瘸子说的地位走,觅到那栋屋子,见门前空空一片,连一根钉子都出有。房前房后往返了转了几圈,踮着足尖往窗户上看,灯光下的不锈钢防匪窗,里中不像是新换的。再细细观察左邻左舍,谁家也没个施工的消息。李大这才清楚是被瘸子耍了,逝世瘸子遛他高兴呢,来日让栓子去整理他。
李大往地下吐心唾沫,躬身走了几步,不情愿,倒返来,躲开保安常走的线路,专往安静的角降去,眼睛尽管扫着小洋楼门前的渣滓袋。刚走几步,好点碰到一棵小树,慢停,本来是一对男女,搂成了一个影子正亲切。李大慌忙绕开,却见中间另有棵树,树是真的,树下有个垃圾桶。
他把手伸进去,一把摸着个硬包包,用力拽出来,在路灯下打开一看,是顶蚊帐。李大夹着蚊帐喜孜孜往回走,心里的气儿消了一泰半。
你说这城里人,咋不知道把坏了的家什修一修再用呢?李大在心里嘀咕。城里人就知道糟尽东西。听说这秀水花园每天往外运垃圾,一车垃圾就得交给垃圾场好几十块,这世上哪有花钱往外扔东西的呢?
今儿买了件衣服,明儿不穿就扔了;买一大盒子左拆右拆折腾到最后拆出一粒屁大的东西,余下一大堆塑料泡沫,兴品站都不收;人活了一生,白入夜夜地挣钱,就为了把钱变成垃圾?你看看那城里马路上跑的汽车,没几年都报废成废铁了;盖下的楼房旧了,一声爆破都成了碎砖烂瓦;饭馆餐馆好好的鸡鸭鱼肉,一大盘一大盘地剩下:哗哗往泔水桶里倒;娶的女人生下了孩子老了丑了,汉子就把女人像垃圾一样扔出去了……这个闹轰轰乱哄哄叫人头晕的都会,说白了就是一座专门出产垃圾的工场,李大愤愤地想。可不像老家,再早些年,人都不知道啥叫垃圾,只要是这地里长出来的东西,都能回到地里去。麦秸玉米秸当柴禾、麦皮玉米皮养猪、菜叶剩饭喂鸡、骨头喂狗、猪粪鸡粪是好肥、穿烂的衣衫,做成鞋壳壳尿布片片;就连化肥口袋都能做裤衩子。屋里扫下的那点碎渣碎土,都挖灶坑烧火了……
李大一活力,只顾往前走,遗漏了好几个垃圾桶,这才把脚步放慢了。转念想想,觉着自己刚才的主意也不全对。城里没有垃圾了,李大进城干啥事情呢?若是城里没有垃圾,城里不就得更名儿叫农村了嘛。再说城里就是比农村的生涯好,好就幸亏城里人能把好东西变成垃圾。谁家只要敢扔垃圾,谁家的日子准保就好过得不可;你还真别小瞧这垃圾,充裕了才有垃圾,有了垃圾就富裕;越富裕垃圾越多,垃圾越多就越富裕。要是能把这城里的垃圾通盘都搬回老家去,一个县的人都能受用好几辈子。你看老家的人,这几年有了点钱,垃圾就一天比一天多了,远近河沟里都是塑料袋,给树权子都戴上了套,风一刮,满天洒纸钱儿,都富饶到天上去。人说金山银山,李大没见过,李大只知道
城里的垃圾是他的金山,挖一锹是一锹,每天挖山不行,子子孙孙是没有贫尽的。
李大痴心妄想着,忽然一脚踢着个啥,呲地溜边上去了。李大蹲下身子,用手四处探索,一摸一手土,再摸,就摸着个凉凉的硬家伙,有烟盒一半大。李大心里一动,三两步跑到路灯下,把手里的东西举起来,照一照,天妈哟,要啥有啥,果然是个手机!
真的假的呢?不会是个玩具吧?李大一时有点吃不准。掂在手心里,没点分量,银亮亮的壳儿,轻盈得很,一巴掌就握住了。他晃了晃,没啥消息;摇了摇,也没动静。李大心里打算,要是个真手机,毕竟是好的还是坏的呢?假如是好的,咋就扔在这路上了?是坏的,拣了还得费钱去建?拣下这个手机,能给谁打电话呢?还得交电话费…..
他在路边的水泥牙子上坐下来,把手机在手心里翻来倒去,像拣了一只烫山芋。
热不丁地,那只山芋在他手古道热肠里沉轻发抖起来,松接着收回了响声,吓得李大差点没把它扔出去。声音愈来愈大,像是一只播送喇叭,扯着嗓子到处声张。夜里的秀水花圃,静得近远的蚊子叫都能听见,更加隐出那响声刺着耳朵的闹。李大死死地捏住了那只小匣子,恨不克不及把它的声音掐死。但李大掐不死它,它只瞅本人响得震天动地,像一只会唱歌的蝈蝈。这会儿李大总算听浑了,它真的是在唱歌,翻来覆去就唱着那末一句词儿:
北京的金山上,广州搬家网,光辉照四方……北京的金山上,毫光照四方……
李大慌了神儿,不知道咋样才干把声音闭上。汗都干了手掌,也没找着个按钮。
就这么来回唱了几遗,响声总算是歇了。李大紧口吻,刚把手机往裤兜里揣好了,就听到有脚步声嗒嗒地跑了过来。一个圆脸保安一边跑一边冲着他摆着大手电筒:喂,您,把手机交出来!
李大紧随着就末路了:手你个鸡巴,在哪呢?你见着是我拣了?
保安推下脸说:我都闻声手机响了,还不否认?
李大也横着:听见了?这会儿它咋不响呢?你让它响个我听听!
正说着,李大的裤兜里就有了响动,彷佛李大身上安了个灌音机:
北京的金山上,光泽照四方……
李大慌忙去捂,那保安手快,伸进李大的裤兜,一下就把手机取出来了。那方脸小子麻利打开盖儿,对着手机就喊:找着了,快过来,就在十八栋楼东南角上。
李大有些发懵,才明白那唱歌是在报信儿。纷歧会儿,一阵噔噔的脚步声,一男一女气��跑来。保安把手机交给他俩,问是否是这个。
那男孩把手机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一会儿,连声说是。女孩减一句:用这老歌儿做手机铃声,咱唯一份儿,没错。两人都说完了,还不走,问保安是怎样找着的。保安指了指李大,说要不是手机铃声音,他还不认账。
女孩冲着李大尖声嚷嚷:你此人,不知道人家丢了东西正焦急呐!男孩细声大气说:谁知道是拣的还是偷的呀,方才我就见这老头鬼头鬼脑地转游,从咱们身旁掠过……说着说着,扬起胳膊冲着李大的胸口一拳打来,李大闪身一躲,拳头打在了肩膀上。李大只觉得身上的血都开锅了,要从喉咙里喷出来,拳头攥得抽筋,晨着那小伙扑过去,却被保安一把拽住….
李大满身哆嗦,说话都结巴了。李大说你们不能委屈人,这手机是我在路上拣的。我每天都在小区拣东西来着……他一急,就把夹肢窝下夹着的蚊帐,掏出来在手里抖了抖。见仨人斜一眼蚊帐,都不消好眼色看他,李大进城半年,看多了这样的眼色,赶快换个说法:你们可不敢瞎扯,偷是 一码事,拣又是一码事,拣的就是拣的,谁拣归谁;拣的就不是偷的,偷东西可犯法,咱就是穷死了也不偷人东西……
那男孩打断他说:坏了的东西,能力当垃圾拣,这手机是好的,你拣了就得还。不还就成了拿,说拿还是好听的,说你偷了,就你这技术,还真提拔你。莫不如像那地铁里的托钵人,跪着伸手供人要,准保不犯罪。
老爷子你要真给我跪下了,我这手机就白送你!
李大憋得说不出话,满身热得火烧个别,恨不砍自己的脸再给那小子两嘴巴。
那手机又开端唱歌:“北京的金山上……”女孩打开手机走到一边去接电话,一时就扔下李大不论。电话说个没完,男孩连忙凑过去,搂着女孩的腰走远了。阿谁方脸保安,操着和李大一样的口音,拉下脸问李大:诚实说,每天你都打哪进来的? 你管!李大嗓子眼里的那股火变成了痰,他狠狠一咳,往绒毯似的草地上吐了一大口,扭头就走。保安跟上来,不紧不慢跟在他死后。李大的气儿没处撒,故意耍一耍这进了城不知自己姓啥的毛孩子,围着楼房转了一圈又一圈,到底把保安跟烦跟乏了,转着转着转没了人影。李大想起了家里熟睡的孙女,这才紧着往栅栏那儿走。走着走着,脚下咣当一响,身子歪了歪,有硬东西撞了他的脚脖。他骂一声娘,停下细看,借着路灯的光,见脚下踩的是一只路上排水用的铁箅子,翘起一角,擦破了他脚上的皮。李大,看就明白,有人把这铁箅子的四边都撬开了,就等着午夜往外搬。李大往铁箅子上蹬了一脚,低头站了一小会,再探头小心往四处观望,夜气上来了,路灯都打盹了,几步外就看不清啥。李大一咬牙,弯腰把铁箅子捡起了,一步步拖着走。总算塞到了栅栏的缺口外头,再用蚊帐裹了,扛上了肩,一路小跑,往村里的租屋走。计算着明天找个远处的废品站卖了,能卖好几块钱。他一边走一边嘟哝:你个小兔崽子,我让你知道知道,啥叫偷啥叫拣啥叫拿!明显是我拣的,你
非好我偷,我就偷个给你瞧!我不偷黑不偷,哪天愉快了,咱还抢银止呢!
李大出一身汗,把铁箅子弄回了村里。见屋里乌着,晓得儿子还没回。掏钥匙开门,没等插里头,锁头就开了。内心疑惑,微微排闼进屋,广州起重吊装。没摸着灯绳,只感到头顶上空空的,像是少了啥。灯明了,李大脑壳嗡一下,懵在那边——
杆子上那一溜十几只鼓饱的塑料袋,一只都不见了。似乎电线杆上停的一群黑鸦,吸啦啦全飞走了,连一只皆不剩。他愣一会,急忙哈腰往木板床底下看,一眼扫往,床底下也齐空了。那三只包得结结实实的编织袋,囫囵个女没有睹了,天上只留下几讲拖拽的土痕。李大再趴低些瞧,床底下实是啥也不了,空空的能躲下好几头老母猪。
房子一下宽阔了很多,犹如栓子刚接他下火车那会儿。李大辛辛劳苦攒了多数年的好东西,一夜全丢了。那可都是有效的东西,李大体弄回故乡去,分给百口人的东西。咋的说没就没了?说拿走就拿走了?这不是拿,是偷;不是偷,是抢!抢李大拣来的东西,丧良知啊!
李大眼前晃过瘸子的影儿,又点头。一个瘸子,咋能挪动转移这么些东西?
木板床上,妮子还在熟睡。李大使劲晃她也不醒,看模样打雷都打不醒。李大一朝气,把床单枕头一把掀了,妮子掉在地上,总算把眼睛展开了。李大问妮子瞥见甚么人来过,妮子一个劲揉眼,想了一会,说梦里来了好几个生蛋老人,都说着老家那处的话……
李大逃出门去,外头黑乎乎一片,连个鬼影都不见。
李大抱着脑袋蹲下来,屋子里脑袋里满是黑乎乎一片。这村儿邻近四处都有老家来的人,说是打工,谁知道都干的啥谋生?那些人,就是牵走一条活牛都不带作声儿的,只能怨自己不早些防备着点儿。李大遇人总说自己拣的不是破烂儿,是好东西!还真让李大说着了。看来别薯的那点垃圾,还不够老乡们分的,还真有人比他更缺垃圾呢。此前从没听说过还有人偷垃圾的,但李大就被偷了。李大被人偷了,阐明李大比老乡们都富裕;李大被人抢了,更解释李大比人富裕。李大进了城,不讨要不偷摸,闷头拣啊拣的,最后拣了个贼。李大不知自己是该
赌气仍是兴奋……
妮子爬到床上,倒头又睡着了。那些偷垃圾的老城,看来是没动妮子一指头,算是留了一半良知。再说,幸亏那些素日卖赝品攒下的钱,早都交给栓子藏好了。李大这样一想,心里好受了些。
他推门出去,背着手在村里转游。月亮从云里钻出来,小河对面的那个体薯,像是盖了一块大大的塑料薄膜。李大想起自己半年前分开李家庄的情况,前三鼓他悄没声地起了床,去了趟自家的麦地。月亮比他到得早,一盏大灯笼似的高悬着,把周遭十里八里的庄稼地都守住了。亮晃晃的月光下,村口的麦地也仿佛蒙上了大片大片的塑料薄膜,晚风一过,平坦展哗啦啦地响动,面前只一片银亮亮滑溜溜的白浪,不见白天里那麦苗翠生生的绿了。李大在地头蹲下身子,伸出一只手,去揪掀那些塑料布。一摸一手空。伸手再一撩,塑料薄膜被风吹化了,手掌里竟是满满的一把麦苗,密密匝匝地攥在手里。尖细的叶片从老夫的指缝缝里钻出来,一把把短剑似的扎手。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涩涩凉凉的叶片,只一会儿就松开了手。嫩老的麦苗,被他那样糙蛮的指头用力一捏,弄欠好就把化肥给捏出来了。如古的玉轮也不是个正经月亮了,把麦地都弄成个塑料大棚模样了,妄哄人哩。李大嘀咕着,站起家来,心里倒有几分喜兴。他掂的不是青涩的麦苗,明显是沉沉的麦穗儿;矮壮壮肥嘟嘟的麦地麦苗,实着实在卧在他脚下,如果把耳朵贴在麦苗的根根上,能听见麦秆快快当当往上蹿个头的声音。眯上眼,就见金黄色的麦粒儿像小河涨水正常到处淌着,把十五的月亮都比下去了。
麦生了麦支,收完麦子种玉米,半年一晃,玉米就该收了……
李大在一个土堆上坐下来,瞧着半边月亮,忽然眼眶子发酸。眼看着就要回去秋收了,可他两手空空,啥啥也没攒下,只剩下了腕上这只手表,给了锁子,链子就不干了。一块手表还能掰两半?咋办呢?只好等着秋收以后再回城里,设法儿另拣上一只手表给链子……
这么说,秋收完了还得回?他问自己。可不回城里还能去哪呢?归正这别薯的垃圾每天有,不拣白不拣。只有呆在城里,金山银山,光线万丈。李大哼哼了一声,觉着那手机上的歌儿耳熟得很,如同良多年前在哪儿听过?他吃力地想了一会,倒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